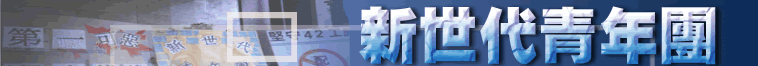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5.04.17
簡評張正修《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發展》
徐文路(台灣《資本論》研究會 常務理事)
對《資本論》的研究,近年來有一股小小的風潮,在台灣學術界和社運界吹著。總體而言這是好事,但是要能真正掌握住《資本論》的核心觀點及其特殊的研究、敘述方法卻不容易。本文在此以張正修所編著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發展》為例,作一概要說明。由於本書所論的枝節甚多,本文先以其第二章第一節有關商品分析的內容進行討論。
張文一開頭在說明「資本主義的基本型態」時,就出現問題:
一、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徹底的商品經濟為其基礎……商品交易是在不同社會進行交易時所發展出來的。 [1]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實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其物質財富是「徹底的」商品經濟。相反,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正文第一句話便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2]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的物質財富主要是以商品的型態出現,但不表示完全沒有非商品的物質財富,因而人們的經濟生活也不可能是「全面依靠」商品的交易來進行。
其次,根據《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交換過程」的分析,商品交易是在不同的原始共同體之間的邊緣地帶出現、發展的,而這個共同體內部,是沒有商品交易的,沒有私有財產的,而由於這樣的外部交易的反作用,這些交換回來的商品在各自的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3]但不能說是「古時候共同體社會的」(古時候是多古?這個共同體的經濟型態又是什麼樣子?),或者是不分任何時代、「不同社會進行交易」時出現的。
二、不同社會的不同生產物,不問其背後的社會秩序為何,基本上,它們都是透過自由、平等的交易而被互相交換。
在此,我把「社會秩序」姑且理解為「經濟型態」,否則分析起來就頗為複雜,作者所要作的說明也就更為漏洞百出。商品交換在歷史上許多時候並不是那麼自由、平等。相反的,商品交換之間的量的比例和關係,要經由千百萬次的交換之後才會慢慢取得,而這樣的比例和關係卻是商品能夠自由、平等交換的前提。
三、隨著商品經濟與商人勢力不斷滲透並擴大至社會內部時,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各種社會秩序即不斷面臨崩潰。
資本主義以前各種社會秩序,並不一定是被商品經濟所破壞:俄國的農村公社一直存在了千年之久,一直要到社會主義時期集體農場建立之後才被破壞;羅馬帝國的奴隸經濟型態,先是被大地產和高利貸(後者嚴格說來,還不屬於現代意義下的資本,因此不是商品經濟或資本主義的力量),後是被日耳曼的封建經濟型態所破壞。二者都不是商品經濟所破壞的。
四、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的特性既然是以外來而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所特有的商品為基礎而形成所謂的市場經濟,那麼其結構的根本原理──商品,自然是經濟學研究的第一對象。
張文特別強調商品相對於原有社會的外來性,除了本引文之外,在此前也出現過。可見作者並不了解上述所謂商品的反作用,同時更顯示出作者在這樣的分析中並未區分「資本主義社會型態」與「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型態,是邏輯分析的對象,是以資本的存在為前提,而資本的存在,是以雇佣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範疇的存在為前提,光有商品是不足的。[4]而資本主義時代,嚴格說來是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時間為起點的。一般把十六世紀作為資本主義的開端,原因主要是由於直到那時,世界貿易出現、世界市場出現、因而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出現。[5]但是有一點必須說明,光有這些還不足以使當時社會財富的共同表現──貨幣──成為資本,或者說具有現代意義下的資本的力量,還須要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之後才算數。
其次,商品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對象,具有其特有的性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以商品為其研究的起點,理由是「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6]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原理可以從商品的分析中找到,那是對的;如果直接把商品當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原理,就變成風馬牛不相及了。
最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一般,而不是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的生產方式,現代主流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更把資本主義特殊的生產方式當作人類永恆的生產方式來研究,因而許多資本主義社會型態所特有的範疇,如資本和市場,被看成是自古即有、發展自今、任何社會型態皆存在。這種荒謬的看法,正反映了主流經濟學的庸俗性和御用(或者也可說「資用」)性。
總的說來,張文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型態的說明,除了用詞上的不嚴謹之外,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區分清楚作為邏輯分析對象的資本主義社會型態與作為歷史階段的資本主義時代。因此,在說明或簡介所謂資本主義基本型態時,常常混淆了這兩個部分。
------------------------------------
接下來,張文大致依照《資本論》第一章的章節順序,企圖說明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以及價形式的發展。不過還是有許多問題。
一、商品必須是為了滿足他人的使用價值被生產、被交換,亦即商品須具有社會性的使用價值。
一方面,使用價值就其性質而言,即使不具社會性仍可實現,因為它是產品的自然屬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商品,使用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由於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確必須有社會承認的可能性為前提,但是否成為可能,要透過交換才能証明,而不是必然會有社會性。[7]因此,商品在尚未進入流通領域前,使用價值的社會性還不能確定,只能說有社會性的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
二、商品彼此間有一定的交換比例,對於商品這樣的性質,我們稱之為「交換價值」或簡稱為「價值」。
價值不是交換價值的簡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及其表現形式出發,分析出商品的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是資本主義社會實體的結晶,而交換價值是它的表現形式。由於價值看不見、摸不著,是像幽靈般的對象性,因而人們只能透過這樣或那樣的表現形式才能看到。
三、任何勞動在「勞動力支出」這一點上其實是共通的。
在這裏,「任何勞動」應指「任何具體勞動」,語意較為清楚。事實上,張文的許多論述過於簡化,很多環節未能說清楚,比如「馬克思認為商品交換的比率應是由商品的另一種性格──亦即商品是勞動的生產物──來決定」,這句話說得未免太輕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特別強調:「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証明了的。」[8]並且花費許多篇幅說明,其間把如何從商品的二重性出發、把具體勞動捨象而得出抽象勞動、說明各自的質與度量問題、彼此在勞動生產力變化時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等等,都清楚說明。而作者卻把這麼重要的部分簡單帶過,這是很危險的。
其次,作者並未對「勞動力」多作說明──每個新的範疇或名詞出現時,作者大多沒作說明──。退一步來看,把抽象勞動說成是「勞動力的支出」當然可以,但是總得先等到把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分說清楚之後再講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此是混淆的,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是。然而這樣的混淆,在理論上是有嚴重後果的:無法正確區分勞動和勞動力,那麼就無法區分「勞動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因而就無法說明工資的虛幻性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如何被掩蓋的。[9]
四、商品的交換價值僅能以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加以顯示,而商品的交換價值透過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加以表示之形態,我們稱之為價值形態。
商品的價值形態或價值形式,發展到貨幣形式之後,產生了新的範疇即價格,到這時,商品已經不再是以其他商品的自然形式來表現。
五、這種價值形態(指擴大的價值形態)並未在所有的商品的世界中取得其市民權。而由於擴大的價值形態有這種缺點,也因此產生了第三種的價值形態(即一般的價值形態)。
如果我們把張文所說的「市民權」,理解為表現一切商品價值的代表性,那麼恰好相反,正是由於在擴大的價值形式中,原本處於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對於那些手持不同商品欲與手持相對價值形式商品的人交換時,這個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在這些人眼中,成為了他們各種商品的共同的價值表現。因而,由於擴大的價值形式的出現,處於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和處於等價形式的諸商品產生了換位,諸商品現在取得了相對價值形式,而倒是原本處於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成了他們的共同的價值表現,變成他們共同的等價形式。從擴大的價值形式到一般價值形式的轉變,等號的兩邊(相對價值形式與等價形式)的變化是相適應的,而非單線的:「等價形式的發展程度是同相對價值形式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但是必須指出,等價形式的發展只是相對價值形式發展的表現和結果。」「價值形式發展到什麼程度,它的兩極即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之間的對立,也就發展到什麼程度。」[10]
六、商品的價值就用貨幣加以表示,即用價格的型態被加以顯示。
此時的貨幣具有兩種職能,即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而不是只有價格標準這一部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說得很清楚:「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價格標準,貨幣執行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價值尺度﹔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價格標準。作為價值尺度,它用來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價值變為價格,變為想像的金量﹔作為價格標準,它計量這些金量。價值尺度是用來計量作為價值的商品,相反,價格標準是用一個金量計量各種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個金量的重量計量另一個金量的價值。」[11]
總結這些問題,可以發現,張文對商品的分析,主要是依據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即包括一、二、三章),但是卻對許多重要的概念和範疇予以庸俗的理解,甚至是任意的誤解,如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把價值當成是交換價值的簡稱。不理解這些重要問題,很難說作者已經理解了《資本論》中對商品的分析。
其次,作者由於「參考」許多日文作品,反而沒有對照《資本論》本身(至少沒有表現在註釋上),因而許多名詞的用語不是很恰當,加上這些用語出現時未作進一步說明,有的還可以從其語義中猜測大概的含義,有的則只能「大膽假設」,如「勞動力的支出」、「市民權」等。
[1]張正修編著,《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與發展》,台北:保成出版社,2001。對張文的引文皆出於本書之第二章第一節,不再加註。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社,1975),頁47。
[3] 前揭書,頁106。
[4] 詳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出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8。
[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167。
[6] 前揭書,頁47。
[7] 前揭書,頁103-104。
[8] 前揭書,頁55。
[9] 詳見前揭書第六篇「工資」。
[10] 前揭書,頁83。
[11] 前揭書,頁117。